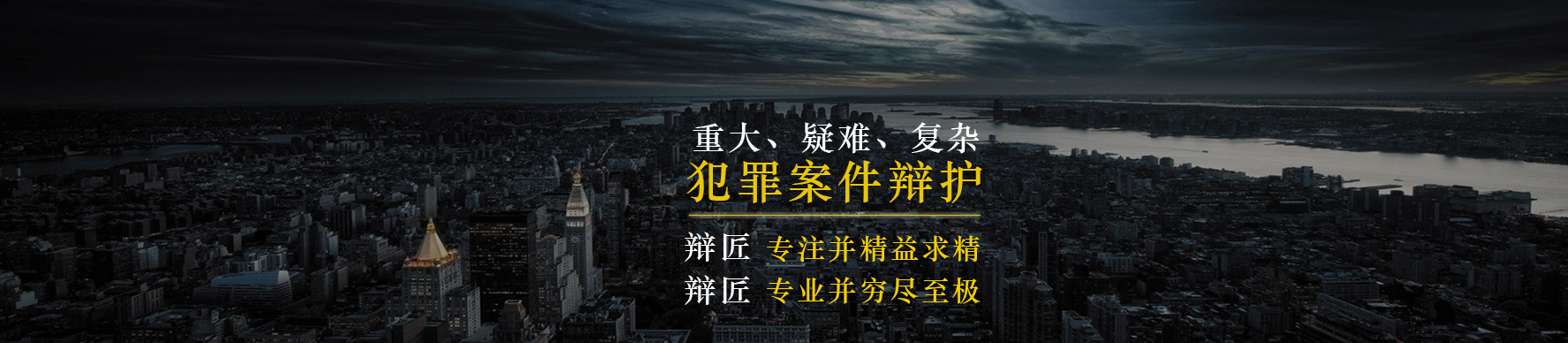
猥亵儿童罪中“从重情节”及“证据采信”之实证研究
2020-01-18
猥亵儿童罪中“从重情节”及“证据采信”之实证研究
导语:
“猥亵”一词介入“暧昧与强奸”之间,属于“暧昧”与强奸的过渡地带,因此,立法上猥亵儿童罪区别于强奸罪,猥亵往往情节轻微,不具有暴力性,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较低,罪与非罪的界限也较为模糊。该罪保留了“流氓罪”的旧有痕迹。司法实践中,该罪名存在“公共场所认定难”、“猥亵定性难”、“证据采信难”、“其他恶劣情节界定难”等4大疑难问题,仍需要司法者作出不带价值倾向的司法裁断,也需要律师摒除社会舆论与整体氛围的干扰,坚守法律人之良知、信仰,为当事人之行为性质精准辩护,以捍卫《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之原则,防止被告人违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被有罪化。
下面笔者将结合亲办案例,对猥亵儿童罪中“从重情节”及“证据采信”尝试做分析论证,以期理清猥亵儿童罪与非罪的界限所在,让行政的归行政,刑事的归刑事,让该罪名焕发其应有的生命力。
一、问题提出:从一起辩护案例谈起
2018年8月16日13时许,居住在xx市xx区的被告人刘某准备出门散步遛狗,便乘坐电梯下楼,遇到了独自下楼的被害人王某(女,六岁)。电梯到达一楼后,两人先后走出电梯,被告人刘某乘着一楼大堂无人之机,从后面搂住了被害人,并用手在隔着衣服的情况摸了被害人的脸和屁股,期间并无暴力行为,未对被害人王某造成生理上的实质伤害,前后大概十数秒的时间后,被害人的母亲从另一部电梯出来发现上述情况,遂报警。公安机关于当日在小区内抓获被告人刘某,并于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笔者在对以上案例的辩护中,归纳出如下法律之焦点问题:
1.定性疑难:该案系行政违法行为or刑事犯罪行为?
2.定量困境:若该案构成犯罪,是否属于《刑法》2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
3.证据疑难:该案的直接证据缺乏,仅有被害人的2次询问笔录以及楼道监控视频所留下的视听资料(电梯内的视频缺失,仅拍到被告人的背面,被告人的手部动作被其身体所遮挡,无法看清),如此,被害人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如何评定?
二、社会观察:猥亵儿童罪之社会情绪剪影
孩童,天真烂漫,承担着厚重的社会期待,同时也凝聚着无数家庭的爱与希望,得到了不尽地偏爱,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性侵,每个百姓都想回避的话题,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不仅是生理性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创伤,可以摧枯拉朽般地彻底毁掉百姓心中建造的安全感、自我认同感,从而产生应激性心理创伤。
如此,当“孩子”与“性侵”两个词同频出现时,家长们对孩子的爱可以轻易地引发起对受害孩童之共情,将其转化为对儿童性侵者的痛恨与愤怒,形成强大的情绪势能,挑动起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可以说,家长们对自家孩子有多疼爱,对儿童性侵类者便有多痛恨。
然,事与愿违,与公众情绪相对立的现实:猥亵儿童类的犯罪数量日益增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中,猥亵儿童案件增长20.49%。2019年,全国法院共一审审结猥亵儿童罪的案件达4159件,而2015年至2018年四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总共也才11519件。
鉴于以上统计案例数据折射出的“性侵儿童类案件”的社会问题及法律问题,笔者结合司法辩护实战经验与感悟,绕过上述两种力量之情绪与利害的博弈,独立于舆论与情绪,谈一谈法律人对‘性侵儿童罪’之法律规定的理性坚守与思索。
三、法律争鸣:猥亵儿童罪之法律适用疑难
针对以上司法问题,笔者认为讨论具体问题前,我们有必要理清目前我国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法律规定,以便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展开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中:“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规定从重处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进行了解释。2015年10月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做了重大修改,将保护对象扩大至成年男性,罪名相应调整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同时在第二款增设了“其他恶劣情节”这一加重处罚情节。
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猥亵儿童罪的客体主要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权,既包括男童、亦包括女童,而犯罪行为方式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法定加重情节有三种:①聚众;②公开场合;③其他恶劣情节。
众所周知,法律之生命力在于影射当下生活、经济等时代缩影,以上法律规定,笔者在司法辩护中发现,该规定更多的保留了80年代的时代烙印,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已经显现出其“弊端与适用困境”。
(一)“公共场所”认定与适用疑难——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之紧张关系
虽然我国《刑法》237条规定“公共场所”为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在面临具体个案时,却让法官陷入了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如何平衡之两难境地。即如果严格适用,坚持制度理性,将可能产生形式法治的错误,无法做到罚当其罪。此道理不难理解,原因在于,该条的规定仅仅是界定了犯罪的发生场所,将其定为法定加重情节,然而案发场所与案发行为的严重性,在本罪中却并未呈现出强相关性。试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在私密空间内,其实施了较为严重的猥亵行为,例如对儿童实行了鸡奸、扣摸私处等伤害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或心理伤害。此时,对其加重处罚也未尝不可。相反,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仅是在地铁上等公共空间,其利用拥挤的环境有意地触碰他人的胸部或者臀部等敏感部位,则从实质法治考究,笔者认为应纳入《治安处罚法》的评价范畴,如果判决定为强制猥亵罪并科以加重情节,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则明显与一般人的法感情产生强烈的冲突。且看《刑法》中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尚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地铁揩油的行为仅仅因为案发地点在公共场合,便以5年为起刑点,笔者认为该立法逻辑,有违罪责刑相适应之原则。
进一步,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意见》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却未从实质上解决上述“司法困境”问题。按照《意见》规定:只要场所具有相对公开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场,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从立法文意解释视角分析,该《意见》完全未考虑猥亵行为的情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一味的拘于法律条文逻辑,而不做出必要的实质解释,势必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判决结果。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在“公众场所”当众实施猥亵行为,常常标准不一、解释多样,其逻辑并非以法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进而得出结论。而是先对行为严重与否做出定性,倘若情节轻微而又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便尽力将所在场所解释为非公共场合,其目的便在于维持刑法的实质合理,而对形式法治做出了正当偏离。换言之,“情节轻微”则“宽松”解释公众场合;“情节严重”则“严格”解释公众场合。这已经背离了“先定性、再定量”的法律适用逻辑,完全为了实质法治而“随意”解释“公众场合”。
追本溯源,之所以猥亵儿童罪中“公共场合”的认定产生此种司法困境,形式法治和实质性公平之间存在这种紧张的关系,原因应从立法背景中找寻答案。猥亵儿童罪脱身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刑法》(1979年)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当中即包含了公然猥亵的侵害行为,但1997年在新修订刑法时则取消了“流氓罪”的条文,进而代替的是相关猥亵类罪名被分散到其他法律条文中,如“强制猥亵、侮辱他人罪”被规入到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中,“聚众淫乱罪”被规入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将公开场合作为加重情节则来源于1984年两高所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规定了侮辱妇女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例如:……2.在公共场所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妇女时造成轻伤的;3.在公共场所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屡教不改的;4.用淫秽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多人,或人数虽少,后果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公开猥亵妇女引起公愤的。
根据上述分析,从犯罪情节考察,在公共场合的一般猥亵行为与在封闭空间内部的恶劣猥亵行为相比,前者未必比后者恶劣。而事实上,考虑到犯罪人的主观心态和社会的普遍氛围,往往在公开场合的猥亵行为受制于客观环境,其行为程度较为轻微,而处于私密的封闭空间,犯罪分子更有胆量采取更恶劣的猥亵行为。而猥亵儿童罪在立法上却偏偏将公开场合作为法定加重情节,无疑残留了流氓罪的痕迹。流氓罪之所以将公开场所作为法定加重情节,是因在不特定人员出入、人流量大的场所公然实施猥亵行为,可见犯罪人的动机卑劣,主观恶性较大,容易触犯众怒、引起公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保护法益的落点是社会的善良风俗,而非公民的人身权利。此立法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天眼系统的普及、人们性观念的解放、人们素养的提升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变迁,“公共场所”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已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显然已经格格不入,这也有悖于1997年刑法将猥亵罪从扰乱社会秩序犯罪中分离中来,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予以规制的立法取向。
回归到本案中,刘某在离开电梯后,从后拥抱受害人的行为仅仅有十几秒,而且隔着衣物触摸,行为无明显暴力性,为偶发性犯罪。倘使认定为具有公共场合的加重情节,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显然处罚过重,不符合一般人对于法治公平的认知,严重违背人们的法感情。因此在对一楼大堂是否属公共场所解释时,应当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方式,不认为其具有法定加重情节。但是若严格参照《意见》之规定,一楼大堂发生的行为显然有被他人感知的可能性,可以为解释为“公众场所”。从这一角度看,本案中刘某的行为不具有法定加重情节,确实是法官与检察官在考量了整体案情后采用较为宽松的解释方式,这也侧面反映了这条规定与实质性公平之间紧张的关系。
(二)“其他恶劣情节”认定与适用疑难——边界模糊不清、无法比对参照
《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修改为强制猥亵他人、侮辱妇女,在原两项加重处罚情节之外,增加了“其他恶劣情节”的规定,拓展了犯罪圈,扩大了刑罚的辐射面,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是颇具价值的立法修改。
然而,虽然在打击犯罪的层面上扩大了辐射面,为法院针对那些较为恶劣猥亵行为的严处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同时其界限不明,也给了法官依据个人的主观判断留下了更大自由裁量的空间。
一般而言,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因为其固定性而就具有了相对的滞后性,况且法律制定者受主观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也无法准确预知法律所要规范的所有可能与情形,所以就有必要通过这些兜底性条款,来尽量减少主观认识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法律缺陷,以及为了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使执法者可以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客观需要,将一些新情况等通过这个兜底性条款来予以适用解决,而无需修改法律。换言之,《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其他情节”是兜底性条款,其作用在于补全列举式立法模式的不足之处。
然而,此类兜底性条款范围的界定标准往往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进行确认。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时的严重情节则应以前文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致人死亡”作为参照,与前文所说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相当性。而在猥亵儿童罪中,前文的加重情节为公开场所与聚众,在立法目的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无法为“其他严重情节”提供参考的依据和标准,在法官断案时,界定“其他严重情节”无从参考,极大的增加了法官主观擅断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猥亵儿童罪牵涉到较为严重的道德判断,如在背景介绍时所言,家长们对孩子的疼爱可以轻易地引发对受害人的共鸣,将其转化为对儿童性侵犯罪者的痛恨,形成强大的势能,挑动起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法官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无法完全剥离自身其他的社会角色,如父亲、母亲等身份角色,在断案时较为容易受到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应当在立法上做出一定程度对法官权利的限缩,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此罪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显然将极大程度的依赖法官自身的价值判断,有畸轻或者畸重的可能性。本案中,明显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此处不再赘述。
(三)定性疑难: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界限模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而根据《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猥亵儿童的行为一旦被定性为犯罪,即使情节轻微的,也往往会被科以8个月至1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如果被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只需要处10-15天的拘留,二者从处罚方式上比较,两者的严厉性相差极大。然而在实践中却无明确的界限加以区分,经常存在重合交叉,这对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其不利。
回归到本案,刘某的行为只是在隔着衣物的情况下,与被害人轻度接触10数秒,且行为不具有暴力性,被害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任何身体伤害。笔者认为上述行为相比较而言,主观恶性较小,不具有人身危害性,且并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15天拘留的顶格处罚更为适宜。但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可见猥亵儿童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较大程度依赖于法官主观上的道德判断、自由裁量之尺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极为不利。
因此,同属猥亵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并不相同。尽管现行刑法规定的猥亵犯罪并未如1979年刑法明示“情节恶劣”等限定性条件,但在司法适用时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对“猥亵”予以适度的限制解释方为妥当。必须综合考虑猥亵手段、针对的身体部位性象征意义的大小、持续时间长短、对被害人身心伤害大小、对社会风尚的冒犯程度等因素,对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予以实质把握。笔者认为我国没有性骚扰的法定概念,但对于一些情节显著轻微的性冒犯行为,作为治安违法的猥亵行为予以处罚是适当的。
(四)证据采信疑难——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判断力较差、各不相同
区别于一般犯罪,猥亵儿童罪由于犯罪者的心态状态与社会上对类似行为强烈的道德规范,一般犯罪行为往往发生在私密的封闭空间里,这让猥亵案件具有了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可由于案件的特殊性质,案发时很少有旁人处于现场,其证言往往只是在事后听取被害人的陈述而产生的传闻证据,证明力非常有限。由此,如果猥亵行为未在被害人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而被告人否认有实施猥亵行为,通常很难认定为犯罪,除非案发时刚好有视频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猥亵儿童罪中仔细审查受害人的陈述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可以成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甚至如果与犯罪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在定罪量刑时,也会较大影响。
那么,如何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进行审查?一般来说,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则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举例来说,如果受害人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信息较为开放,此时不宜以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其认知、表达能力和对性的认识程度。而相反,如果受害人处于贫困山区,信息闭塞,对性的认识程度非常原始,又不善表达,此时不宜轻易地将暧昧不清、闪烁其词的受害人陈述理解为事实不清,而更应当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力图还原案发时的真相。再如,如果受害人前后供述之间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适当引导、有限度的采纳其言辞。
回归到本案的证据中,亦有以上证据采信疑难问题,例如,受害人王某第1次询问笔录被问到被告人是在几楼时上的电梯,其回答说:“记不住了。”然而在第2次的询问笔录中却精准回答:“是在八楼。”按照常理推测,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模糊,受害人并没有道理在第1次询问时记不清楚,而在第2次询问时反而回想了起来。那么,不能排除是否中间有监护人等引导其陈述。对其第2次陈述不应该完全排除可信度,也不能完全相信,应当有限度的采信。这一点在最高检公布的指导案例中也有体现(检例第42号):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四、道德犹存,理性至上——孩童保护与法律敬畏之权衡
我们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发场所与案发行为的严重性,在本罪中却并未呈现出强相关性。所以公共场所做为加重情节经常会产生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判决结果,需要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追求实质性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具体行为的恶劣程度、人身危害程度对公共场所进行解释,正当偏离形式法治。而且,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由于加重处罚情节仅限于“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导致实践中,对于一些严重程度完全不亚于强奸罪的肛交、棍棒插入阴道等猥亵犯罪,以及猥亵手段严重、猥亵人数及次数特别多的犯罪,只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反而一些手段、情节轻微,仅因为发生在公众场合的猥亵行为,被判处了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虽然在《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其他恶劣情节”,新法的施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的问题,对极其严重的猥亵行为,法官可以适用此条,判处被告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虽列举了“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两项加重处罚情节,但该两项情节与刑法增设的“其他恶劣情节”之间缺少实质关联,难以比照该两项情节对“其他恶劣情节”进行解释。缺少了参照对象,将直接导致该条的“其他恶劣情节“的认定主要依靠于法官个人的主观意志,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而由于缺乏明确标准或裁判指引,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猥亵犯罪的量刑把握,仍存在较大差异,情节类似但量刑相差一两年的案例,时有出现。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基本情节与加重情节之间的界限模糊。从法律角度上说,猥亵情节轻微的,应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行政拘留;情节较为严重的,应该根据《刑法》237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则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三者之间的界限却缺乏明确界限,需要法官根据自身的道德观念做出判断,这当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价值判断,也造成了在司法上,处刑严宽不一的现象,伤害了被告人的权利,也让猥亵儿童罪成为了新时期的口袋罪。如本文中所提及案例,其刘某的猥亵行为并未伸手至小女孩的衣物内部,也未拉扯、脱去小女孩的衣服,属于轻度肢体接触。时间上只有十几秒,行为并无暴力性。倘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科以15天的行政拘留,并无不可。然而由于此罪的界限较为模糊,缺乏稳定的统一标准,最终一审被定刑1年6个月,确有不当。本文认为,针对此类案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被害人身份,猥亵手段的暴力性程度,猥亵的身体部位所代表的性象征意义,被害人人数,猥亵次数,对被害人身心伤害大小,以及是否系入户实施等因素,准确判断是否属于猥亵情节恶劣,做到罪刑相适应。
没人对新生的生命不欢呼雀跃,没有人不对天真烂漫的孩童保有爱怜,这种本能的欢喜里蕴含着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法律作为这种本能的殉葬品。在宗教里,只有神可以审判人,但我们没有找到那位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制定了法律,让法官代行这项神的职能。我们当然要保护孩子,可是能否因此而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大刀阔斧,这是法律人需要透过社会现象而反思的实质问题。
概言之,本文并非意在仅为被告人的权利而辩护,而是希望在法律界限模糊时,我们仍可以保持理性,尽可能的排除个人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在猥亵儿童罪中,我们最该警醒:我们的评价与裁断——有没有用个人道德取代法律理性,如果本文可以让大家多一些警醒、少一些情绪,甚至引发几许思考,如斯,法之温情流淌,善莫大焉。
一、问题提出:从一起辩护案例谈起
2018年8月16日13时许,居住在xx市xx区的被告人刘某准备出门散步遛狗,便乘坐电梯下楼,遇到了独自下楼的被害人王某(女,六岁)。电梯到达一楼后,两人先后走出电梯,被告人刘某乘着一楼大堂无人之机,从后面搂住了被害人,并用手在隔着衣服的情况摸了被害人的脸和屁股,期间并无暴力行为,未对被害人王某造成生理上的实质伤害,前后大概十数秒的时间后,被害人的母亲从另一部电梯出来发现上述情况,遂报警。公安机关于当日在小区内抓获被告人刘某,并于一审判决刘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笔者在对以上案例的辩护中,归纳出如下法律之焦点问题:
1.定性疑难:该案系行政违法行为or刑事犯罪行为?
2.定量困境:若该案构成犯罪,是否属于《刑法》2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
3.证据疑难:该案的直接证据缺乏,仅有被害人的2次询问笔录以及楼道监控视频所留下的视听资料(电梯内的视频缺失,仅拍到被告人的背面,被告人的手部动作被其身体所遮挡,无法看清),如此,被害人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如何评定?
二、社会观察:猥亵儿童罪之社会情绪剪影
孩童,天真烂漫,承担着厚重的社会期待,同时也凝聚着无数家庭的爱与希望,得到了不尽地偏爱,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性侵,每个百姓都想回避的话题,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不仅是生理性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创伤,可以摧枯拉朽般地彻底毁掉百姓心中建造的安全感、自我认同感,从而产生应激性心理创伤。
如此,当“孩子”与“性侵”两个词同频出现时,家长们对孩子的爱可以轻易地引发起对受害孩童之共情,将其转化为对儿童性侵者的痛恨与愤怒,形成强大的情绪势能,挑动起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可以说,家长们对自家孩子有多疼爱,对儿童性侵类者便有多痛恨。
然,事与愿违,与公众情绪相对立的现实:猥亵儿童类的犯罪数量日益增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中,猥亵儿童案件增长20.49%。2019年,全国法院共一审审结猥亵儿童罪的案件达4159件,而2015年至2018年四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总共也才11519件。
鉴于以上统计案例数据折射出的“性侵儿童类案件”的社会问题及法律问题,笔者结合司法辩护实战经验与感悟,绕过上述两种力量之情绪与利害的博弈,独立于舆论与情绪,谈一谈法律人对‘性侵儿童罪’之法律规定的理性坚守与思索。
三、法律争鸣:猥亵儿童罪之法律适用疑难
针对以上司法问题,笔者认为讨论具体问题前,我们有必要理清目前我国关于猥亵儿童罪的法律规定,以便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展开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中:“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规定从重处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进行了解释。2015年10月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做了重大修改,将保护对象扩大至成年男性,罪名相应调整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同时在第二款增设了“其他恶劣情节”这一加重处罚情节。
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猥亵儿童罪的客体主要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权,既包括男童、亦包括女童,而犯罪行为方式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法定加重情节有三种:①聚众;②公开场合;③其他恶劣情节。
众所周知,法律之生命力在于影射当下生活、经济等时代缩影,以上法律规定,笔者在司法辩护中发现,该规定更多的保留了80年代的时代烙印,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已经显现出其“弊端与适用困境”。
(一)“公共场所”认定与适用疑难——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之紧张关系
虽然我国《刑法》237条规定“公共场所”为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在面临具体个案时,却让法官陷入了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如何平衡之两难境地。即如果严格适用,坚持制度理性,将可能产生形式法治的错误,无法做到罚当其罪。此道理不难理解,原因在于,该条的规定仅仅是界定了犯罪的发生场所,将其定为法定加重情节,然而案发场所与案发行为的严重性,在本罪中却并未呈现出强相关性。试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在私密空间内,其实施了较为严重的猥亵行为,例如对儿童实行了鸡奸、扣摸私处等伤害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或心理伤害。此时,对其加重处罚也未尝不可。相反,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仅是在地铁上等公共空间,其利用拥挤的环境有意地触碰他人的胸部或者臀部等敏感部位,则从实质法治考究,笔者认为应纳入《治安处罚法》的评价范畴,如果判决定为强制猥亵罪并科以加重情节,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则明显与一般人的法感情产生强烈的冲突。且看《刑法》中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尚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地铁揩油的行为仅仅因为案发地点在公共场合,便以5年为起刑点,笔者认为该立法逻辑,有违罪责刑相适应之原则。
进一步,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意见》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却未从实质上解决上述“司法困境”问题。按照《意见》规定:只要场所具有相对公开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场,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从立法文意解释视角分析,该《意见》完全未考虑猥亵行为的情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一味的拘于法律条文逻辑,而不做出必要的实质解释,势必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判决结果。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在“公众场所”当众实施猥亵行为,常常标准不一、解释多样,其逻辑并非以法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进而得出结论。而是先对行为严重与否做出定性,倘若情节轻微而又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便尽力将所在场所解释为非公共场合,其目的便在于维持刑法的实质合理,而对形式法治做出了正当偏离。换言之,“情节轻微”则“宽松”解释公众场合;“情节严重”则“严格”解释公众场合。这已经背离了“先定性、再定量”的法律适用逻辑,完全为了实质法治而“随意”解释“公众场合”。
追本溯源,之所以猥亵儿童罪中“公共场合”的认定产生此种司法困境,形式法治和实质性公平之间存在这种紧张的关系,原因应从立法背景中找寻答案。猥亵儿童罪脱身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刑法》(1979年)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当中即包含了公然猥亵的侵害行为,但1997年在新修订刑法时则取消了“流氓罪”的条文,进而代替的是相关猥亵类罪名被分散到其他法律条文中,如“强制猥亵、侮辱他人罪”被规入到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中,“聚众淫乱罪”被规入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将公开场合作为加重情节则来源于1984年两高所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规定了侮辱妇女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例如:……2.在公共场所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妇女时造成轻伤的;3.在公共场所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屡教不改的;4.用淫秽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多人,或人数虽少,后果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公开猥亵妇女引起公愤的。
根据上述分析,从犯罪情节考察,在公共场合的一般猥亵行为与在封闭空间内部的恶劣猥亵行为相比,前者未必比后者恶劣。而事实上,考虑到犯罪人的主观心态和社会的普遍氛围,往往在公开场合的猥亵行为受制于客观环境,其行为程度较为轻微,而处于私密的封闭空间,犯罪分子更有胆量采取更恶劣的猥亵行为。而猥亵儿童罪在立法上却偏偏将公开场合作为法定加重情节,无疑残留了流氓罪的痕迹。流氓罪之所以将公开场所作为法定加重情节,是因在不特定人员出入、人流量大的场所公然实施猥亵行为,可见犯罪人的动机卑劣,主观恶性较大,容易触犯众怒、引起公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保护法益的落点是社会的善良风俗,而非公民的人身权利。此立法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天眼系统的普及、人们性观念的解放、人们素养的提升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变迁,“公共场所”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已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显然已经格格不入,这也有悖于1997年刑法将猥亵罪从扰乱社会秩序犯罪中分离中来,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予以规制的立法取向。
回归到本案中,刘某在离开电梯后,从后拥抱受害人的行为仅仅有十几秒,而且隔着衣物触摸,行为无明显暴力性,为偶发性犯罪。倘使认定为具有公共场合的加重情节,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显然处罚过重,不符合一般人对于法治公平的认知,严重违背人们的法感情。因此在对一楼大堂是否属公共场所解释时,应当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方式,不认为其具有法定加重情节。但是若严格参照《意见》之规定,一楼大堂发生的行为显然有被他人感知的可能性,可以为解释为“公众场所”。从这一角度看,本案中刘某的行为不具有法定加重情节,确实是法官与检察官在考量了整体案情后采用较为宽松的解释方式,这也侧面反映了这条规定与实质性公平之间紧张的关系。
(二)“其他恶劣情节”认定与适用疑难——边界模糊不清、无法比对参照
《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修改为强制猥亵他人、侮辱妇女,在原两项加重处罚情节之外,增加了“其他恶劣情节”的规定,拓展了犯罪圈,扩大了刑罚的辐射面,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是颇具价值的立法修改。
然而,虽然在打击犯罪的层面上扩大了辐射面,为法院针对那些较为恶劣猥亵行为的严处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同时其界限不明,也给了法官依据个人的主观判断留下了更大自由裁量的空间。
一般而言,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因为其固定性而就具有了相对的滞后性,况且法律制定者受主观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也无法准确预知法律所要规范的所有可能与情形,所以就有必要通过这些兜底性条款,来尽量减少主观认识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法律缺陷,以及为了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使执法者可以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客观需要,将一些新情况等通过这个兜底性条款来予以适用解决,而无需修改法律。换言之,《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其他情节”是兜底性条款,其作用在于补全列举式立法模式的不足之处。
然而,此类兜底性条款范围的界定标准往往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进行确认。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时的严重情节则应以前文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致人死亡”作为参照,与前文所说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相当性。而在猥亵儿童罪中,前文的加重情节为公开场所与聚众,在立法目的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无法为“其他严重情节”提供参考的依据和标准,在法官断案时,界定“其他严重情节”无从参考,极大的增加了法官主观擅断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猥亵儿童罪牵涉到较为严重的道德判断,如在背景介绍时所言,家长们对孩子的疼爱可以轻易地引发对受害人的共鸣,将其转化为对儿童性侵犯罪者的痛恨,形成强大的势能,挑动起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法官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无法完全剥离自身其他的社会角色,如父亲、母亲等身份角色,在断案时较为容易受到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应当在立法上做出一定程度对法官权利的限缩,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此罪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显然将极大程度的依赖法官自身的价值判断,有畸轻或者畸重的可能性。本案中,明显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此处不再赘述。
(三)定性疑难: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界限模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而根据《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猥亵儿童的行为一旦被定性为犯罪,即使情节轻微的,也往往会被科以8个月至1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如果被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只需要处10-15天的拘留,二者从处罚方式上比较,两者的严厉性相差极大。然而在实践中却无明确的界限加以区分,经常存在重合交叉,这对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其不利。
回归到本案,刘某的行为只是在隔着衣物的情况下,与被害人轻度接触10数秒,且行为不具有暴力性,被害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任何身体伤害。笔者认为上述行为相比较而言,主观恶性较小,不具有人身危害性,且并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15天拘留的顶格处罚更为适宜。但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可见猥亵儿童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较大程度依赖于法官主观上的道德判断、自由裁量之尺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极为不利。
因此,同属猥亵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并不相同。尽管现行刑法规定的猥亵犯罪并未如1979年刑法明示“情节恶劣”等限定性条件,但在司法适用时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对“猥亵”予以适度的限制解释方为妥当。必须综合考虑猥亵手段、针对的身体部位性象征意义的大小、持续时间长短、对被害人身心伤害大小、对社会风尚的冒犯程度等因素,对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予以实质把握。笔者认为我国没有性骚扰的法定概念,但对于一些情节显著轻微的性冒犯行为,作为治安违法的猥亵行为予以处罚是适当的。
(四)证据采信疑难——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判断力较差、各不相同
区别于一般犯罪,猥亵儿童罪由于犯罪者的心态状态与社会上对类似行为强烈的道德规范,一般犯罪行为往往发生在私密的封闭空间里,这让猥亵案件具有了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可由于案件的特殊性质,案发时很少有旁人处于现场,其证言往往只是在事后听取被害人的陈述而产生的传闻证据,证明力非常有限。由此,如果猥亵行为未在被害人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而被告人否认有实施猥亵行为,通常很难认定为犯罪,除非案发时刚好有视频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猥亵儿童罪中仔细审查受害人的陈述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可以成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甚至如果与犯罪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在定罪量刑时,也会较大影响。
那么,如何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进行审查?一般来说,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则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举例来说,如果受害人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信息较为开放,此时不宜以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其认知、表达能力和对性的认识程度。而相反,如果受害人处于贫困山区,信息闭塞,对性的认识程度非常原始,又不善表达,此时不宜轻易地将暧昧不清、闪烁其词的受害人陈述理解为事实不清,而更应当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力图还原案发时的真相。再如,如果受害人前后供述之间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适当引导、有限度的采纳其言辞。
回归到本案的证据中,亦有以上证据采信疑难问题,例如,受害人王某第1次询问笔录被问到被告人是在几楼时上的电梯,其回答说:“记不住了。”然而在第2次的询问笔录中却精准回答:“是在八楼。”按照常理推测,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模糊,受害人并没有道理在第1次询问时记不清楚,而在第2次询问时反而回想了起来。那么,不能排除是否中间有监护人等引导其陈述。对其第2次陈述不应该完全排除可信度,也不能完全相信,应当有限度的采信。这一点在最高检公布的指导案例中也有体现(检例第42号):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四、道德犹存,理性至上——孩童保护与法律敬畏之权衡
我们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发场所与案发行为的严重性,在本罪中却并未呈现出强相关性。所以公共场所做为加重情节经常会产生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判决结果,需要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追求实质性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具体行为的恶劣程度、人身危害程度对公共场所进行解释,正当偏离形式法治。而且,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由于加重处罚情节仅限于“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导致实践中,对于一些严重程度完全不亚于强奸罪的肛交、棍棒插入阴道等猥亵犯罪,以及猥亵手段严重、猥亵人数及次数特别多的犯罪,只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反而一些手段、情节轻微,仅因为发生在公众场合的猥亵行为,被判处了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虽然在《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其他恶劣情节”,新法的施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的问题,对极其严重的猥亵行为,法官可以适用此条,判处被告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虽列举了“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两项加重处罚情节,但该两项情节与刑法增设的“其他恶劣情节”之间缺少实质关联,难以比照该两项情节对“其他恶劣情节”进行解释。缺少了参照对象,将直接导致该条的“其他恶劣情节“的认定主要依靠于法官个人的主观意志,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而由于缺乏明确标准或裁判指引,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猥亵犯罪的量刑把握,仍存在较大差异,情节类似但量刑相差一两年的案例,时有出现。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基本情节与加重情节之间的界限模糊。从法律角度上说,猥亵情节轻微的,应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行政拘留;情节较为严重的,应该根据《刑法》237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则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三者之间的界限却缺乏明确界限,需要法官根据自身的道德观念做出判断,这当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价值判断,也造成了在司法上,处刑严宽不一的现象,伤害了被告人的权利,也让猥亵儿童罪成为了新时期的口袋罪。如本文中所提及案例,其刘某的猥亵行为并未伸手至小女孩的衣物内部,也未拉扯、脱去小女孩的衣服,属于轻度肢体接触。时间上只有十几秒,行为并无暴力性。倘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科以15天的行政拘留,并无不可。然而由于此罪的界限较为模糊,缺乏稳定的统一标准,最终一审被定刑1年6个月,确有不当。本文认为,针对此类案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被害人身份,猥亵手段的暴力性程度,猥亵的身体部位所代表的性象征意义,被害人人数,猥亵次数,对被害人身心伤害大小,以及是否系入户实施等因素,准确判断是否属于猥亵情节恶劣,做到罪刑相适应。
没人对新生的生命不欢呼雀跃,没有人不对天真烂漫的孩童保有爱怜,这种本能的欢喜里蕴含着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法律作为这种本能的殉葬品。在宗教里,只有神可以审判人,但我们没有找到那位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制定了法律,让法官代行这项神的职能。我们当然要保护孩子,可是能否因此而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大刀阔斧,这是法律人需要透过社会现象而反思的实质问题。
概言之,本文并非意在仅为被告人的权利而辩护,而是希望在法律界限模糊时,我们仍可以保持理性,尽可能的排除个人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在猥亵儿童罪中,我们最该警醒:我们的评价与裁断——有没有用个人道德取代法律理性,如果本文可以让大家多一些警醒、少一些情绪,甚至引发几许思考,如斯,法之温情流淌,善莫大焉。
